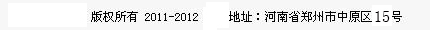因为“亚健康”概念的大众化,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形态学导向,我们现在也把“已病”局限在器质性改变,只有哪个组织器官发生了异常,如炎症、癌症、血脂高、动脉硬化等,才是疾病,如果零件没坏,没有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证据,就不算是病,是亚健康,是健康和病的中间状态。
不少人把中医的“未病”等于西医的亚健康,认为“治未病”就是对亚健康的治疗和调理。我认为,亚健康和中医的“未病”画等号,辨证论治就会发生逻辑问题。
(1)病概念解读。
中医“未病”的概念很明确,就是没有病,但有两个不同的外延,一是从个体生命的整体状况讲,一是从五藏生命单位的关系讲(是五藏而不是五脏),我们要把它们区别开来。
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:“圣人不治已病,治未病,不治已乱,治未乱,此之谓也。夫病已成而后药之,乱已成而后治之,譬犹渴而穿井,而铸锥,不亦晚乎。”
这里“未病”的概念,就是个体生命没有患病,和“平人”具有同样的含义。“治未病”,就是在个体健康的时候,要注意未病先防,法阴阳,和术数,饮食有节,起居有常,动静有度,不过劳,平和心态。“治未病”的人,可以称之为圣人。
《难经·七十七难》:“上工治未病,中工治已病,何谓也?然,所谓治未病者,见肝之病,则知肝当传之于脾,故当先实其脾气,勿令得受肝之邪。故曰治未病焉。中工者,见肝之病,不晓相传,但一心治肝,故曰治已病也。”这里“未病”的概念,就是还没有发生病变的藏腑生命体系,是相对于已病的藏腑生命体系而言的,但是以“已病”的藏腑生命体系为前提,以“已病”藏腑生命体系的传变趋向为依据的。
以肝藏生命体系的疾病为例,没有肝藏的“已病”,就没有“未病”的脾藏,没有“已病”肝藏的传变趋势的具体指向,也没有脾藏的“未病”。当然,除了脾藏,肝藏的疾病也可能传变心藏、肾藏或肺藏,传变趋向不同,“未病”就具有不同的内容,可能是脾,可能是心,可能是肾,可能是肺。同理,卫分受邪了,但病邪还没有危害气分,与卫分相比较,气分尚处于相对健康状态,也属于“未病”。
中医的“未病”和“已病”,是相对概念。健康与疾病相对而言,健康属于“未病”,疾病属于“已病”;患病的藏腑和没有患病的藏腑相对而言,前者属“已病”,后者属“未病”。“未病”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,一是“未病”之躯,一是“未病”之藏(经络气血等)。“治未病”,对没有患病的人来说,就是要加强自己的生命修为,防止疾病的发生;对已经患病的人来说,就是要具有既病防变的积极理念,及早正确治疗,把疾病控制在已病范围,并在这个范围治愈,这是衡量“上工”的标准。
“已病”后,生命反应是多种多样的,脉、色、症、征都有可能发生变化,医生“观其脉症”的四诊水平,“见微得过”的思维能力,决定了判断“已病”和“未病”的可靠性。
《伤寒论》的辨证论治,贯穿了“治未病”的积极理念,“知犯何逆”要求“知”证候病机的传变,“随证治之”要求扭转截断证候传变,使疾病在没有传变之前得到有效治疗。中医控制病情,阻断传变,使疾病在“已病”阶段痊愈的治疗学思想,就是在数百年以后,也不会落后。哪个时代、哪个人,不希望在疾病没有发展变化的时候得到有效治疗?
(2)病在生命时空因应协调性的失常。
“阴阳神气”的反应性调节,是一个十分复杂、个别差异的自稳调控体系,以五藏生命体系为基础,生克制化等相联系,升降出入为活动,开合枢为调节,不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保持春夏秋冬的时空顺应性,而且能够随机应变,适应具体气候的寒热变化,从而保持“形与神俱”的健康状态。“阴阳神气”的反应性调节,不仅决定生命健康状态,而且决定疾病的预后。
《伤寒论》把“阴阳神气”的反应性调节的最佳状态,称之为“阴阳自和”,只要“阴阳自和”,疾病就能够痊愈。
在这里需要说明,“反应性调节”和“反应”是不同的概念。反应性调节是对感应所作出的调节活动,这样的调节机制,同样通过生命的感应,反应于体表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生命现象。先有感应,然后反应,反应和反应性调节可以是同时同步的,也可能是前后发生的,先有所调节,而后有所反应。反应既表现为感应到的东西,又表现反应性调节所作出的调节。风寒外感,发热恶寒的表现,既是外邪袭表的生命感应性,又是生命对外邪侵袭肌表所作出的反应性调节,说明了某种正邪斗争的性质。反应是被动的,反应性调节具有能动性,是目的性的。反应使内在生命活动、疾病危害得以表现出来,反应性调节维护生命“阴阳神气”与时空动态协调一致的“平”“和”状态。(生命的发生形成和进化发展,本身就是被动适应自然的结果,但对于生命而言,适应性却需要主动的调节。因此,生命之“应”既是主动的,又是被动的。)病的形成、发展、变化的实质,是生命感应到外部因素对五藏气血营卫等的平和状态的不良影响后,反应性调节不能适当、适度地加以纠正、消除,使生命丧失了生命时空的顺应性与适应性,“阴阳神气”丧失了“阴平阳秘”之“和”的结果。
自然界的生命,顺应性本于阴阳,和于四时,五藏生命的阴阳和自然的阴阳相因相应。日月运行,四季寒暑更替,成风寒暑湿燥火,在四季交替的基本节律的基础上,具有多样性、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规律,因此,生命不仅形成了固有的反应性调节机制,顺应四季寒暑的更替规律,而且形成了随机的反应性调节机制,对应气候的随机性变化,使生命和自然时空保持因应协调的一致性。这是天人相应的重要内容。只是不同个体,随机调节会有所不同,即使是同一个体,固有调节也有所差异。不同藏腑,主应于不同的季节时空环境,目的在于维护生命“阴阳神气”与外部环境的“阴阳神气”同步性。
以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为例,春天气候转温,草木生发而开花,肝气应之而生命呈现“发陈”的反应性调节;夏天由温而暑热,草木枝繁叶盛,心气应之而生命呈现“蕃秀”的反应性调节;秋天热而转凉,草木果实累累,肺气应之而生命呈现“容平”的反应性调节;冬天由凉而寒,草木叶枯果落,肾气应之而生命呈现“闭藏”的反应性调节。
“发陈”、“蕃秀”、“容平”、“闭藏”,是在生命适应自然气候而形成的固有的反应性调节规律,和自然万物的变化具有一致性,未病之人根据这样的规律,修炼自身的心性和注意自己的生活行为,实现“四气调神”的目的。
如果整个人类遵从这样的生命规律,则能够与“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”。未病先防的根本,就在于维护生命的时空顺应性。
五藏生命体系的整体层面,有五藏自身的反应性调节,也有五藏之间的反应性调节,任何不利因素的生命影响,生命五藏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性调节,以维护五藏生命的和平状态。从一个藏腑的生命体系到另一个藏腑的生命体系,从五藏生命的外层到内在“神机”,“阴阳神气”形成了一道道的维护生命之“和”的防线,疾病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。任何疾病都存在“已病”和“未病”的关系,都存在“已病”的藏腑和“未病”的藏腑,“已病”的生命层次和“未病”的生命层次。辨证论治的根本,就在于维护“未病”而治疗“已病”,反对因为治疗“已病”而伤害“未病”。因为这样的理念,辨证论治是最具生命安全性的临床方法。
未病先防是“治未病”,关键在于顺应自然、适应社会,根据自然环境、季节气候等的变化,调整生活行为,调整自己心态,做到四气调神——春养肝顺生发、夏养心护气津、秋养肺助肃降、冬养肾资藏纳,使自己的“阴阳神气”和自然保持同步。另外,还需要加强个人的生命修养,心态平和、随遇而安,恬淡虚无而志意治,以适应社会、适应家庭等人文环境,就能够维护健康,做一个“未病”的人。
既病防变也是“治未病”,关键在于顺应“阴阳神气”反应性调节态势,不要攻其虚,不要补其实,也不要用寒性的药物去治疗寒性的疾病,不要用热性的药物去治疗热性的疾病,使五藏生命体系、三阴三阳生命层次等自和力不被破坏,就能够维护“未病”之藏的“阴阳神气”,实现“上工治未病”的目的。
(3)亚健康等于未病的逻辑错误。
疲劳、胸闷、头痛、失眠、健忘、腰酸背痛、情绪不安等,是异常生命状况,是病人切身感受到的痛苦,从个体的生命看,属于“已病”范畴。如果我们把亚健康和“未病”画等号,“头痛”、“不寐”、“郁证”属于亚健康而不是病,辨证论治就可能丧失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基础,发生逻辑问题。
中医的病在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之“应”的机制的异常,要是也用形态指标作为疾病标准,中医也就成西医了。“应”则生命,不“应”则死亡。中医“已病”与“未病”,从根本上讲,取决于个体生命的反应性调节,如果“阴阳神气”能够顺应自然,并且随机应变,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喜怒哀乐不急不躁,就可能不病,反之就可能有病。
春天生发,气由内藏的状态逐渐转向外发上升,此时,如果肝血不足,肝气亏虚,清阳之气不能应春天之时而“发陈”,就可能出现疲劳、头痛、失眠等症状。不少人都有“春困”的感觉,为什么“春困”?肝气固有的反应性调节失常,导致生命与春天生发之气的协调性较差。但如果肝的“神机”感应春天之气,能够调节“发陈”状态,清气上升适应春温生发的自然变化,“春困”就会消失。反之,“春困”就会越来越重,甚至因为清阳不能上升,头失濡养而发生头痛、失眠等,疾病就发生了。(脾主升清四时皆然,肝主生发应在春天,其发陈的升清应春时而作。)同样道理,夏天心的气津如果因暑热而外泄太过,秋天肺气因温燥不能降肃,冬天肾精丧失藏纳,都会导致“阴阳神气”的动态平衡发生问题,表现出这样那样的不适感。
“亚健康”是西医学的概念,和中医学的“未病”根本就是两码事。中医是中医,西医是西医,是具有不同概念体系的两个学科。是中医就必须遵循中医的原则规范,服从中医的概念逻辑,具有中医的生命观念。按照西医学的观点,如果没有形态学证据就是亚健康,不是病,那就不属于临床治疗学的范畴。不仅如此,没有形态学的证据不能算病,中医的辨证论治就该否定,因为辨证论治